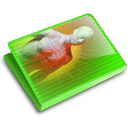|
|||||||||||||||||||||||||||||||||||||||||||||||||||

|
|||||||||||||||||||||||||||||||||||||||||||||||||||
|
|||||||||||||||||||||||||||||||||||||||||||||||||||
人体科学古实验学初探 |
||
|
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史上,有个共同的有趣现象:遥远的天体最先受到注视,而对人类自身,特别是大脑两半球的研究却开始得最晚。当我国出现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并制订出精确的历法时,却始终信奉孟子的“心之官则思”,认为思想是心脏的产物。这也难怪,因为生物电的科学发现才只二百年,比望远镜的发明要晚得多;而人类脑电图的描记,不过六十年的历史。应该说,人类刚刚进入认识自身及大脑这一未知天地之门。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率先报道了大足县少年唐雨能以耳朵认字的消息,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陆续有非眼视觉、脑际信息遥感、特异功能致动等青少年功能者的发现报道。由于这类发现难以现代科学知识去解释,加之当时宣传报道的过热和欠慎重,致使正常的怀疑和立论很高的责难纷起,这使广大群众无所适从,使青少年功能者和严谨的研究者们,蒙受着巨大的压力。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打破了早春的静默,毅然增辟专栏,连续刊登严格的观测报告和有关院校、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发起了两次全国性的科学讨论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1980年夏亲切接见该刊全体人员,给予肯定和鼓励。他指出:各种气功功能态及人体特异功能乃是“人类某种潜在的固有功能的显现。”从而为人体科学这一新兴的科学大部门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既然是人体潜能的显现,就决不是一国一时地地所特有,而应是遍及世界各民族,经常发生的共同现象。这就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各国科技界有识之士的关注。 1882年,在英国以探究脑际遥感(Telepathy,旧译传心术)为起因,成立了国际性的特异现象研究会(SPR)。1982年曾特邀我国的陈信、梅磊两位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百周年庆典。他们宣读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中国》的论文,受到各国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和苏联的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相继开始了对人体潜能的科学实验。1935年,美国杜克大学的专门实验室,首先采用特异心理学(Parapsycholoty,也译作超心理学)一词来定名我们所论的人体潜能研究,简称为Psi或Ψ。1957年,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国际特异心理学联合会,并于1969年被接纳进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 苏联约于1965年成立了类似组织,致力于新型生物物理通信方式的研究开发。其领导人库根教授曾于1969年访问美国,并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它的译文已收入美国政府研究报告之中。 1976年,日本东京也成立了全国性的“真正面向科学”的Psi研究会。他的数百名高级会员多为大学教授或研究员,他们举行年会,出版会刊、杂志,并多次组团来华,同中国人体科学学会进行学术交流。 其实在中国近代,并不缺乏对人体潜能研究的热心者,但在解放前,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这类研究自然提不上日程。解放以来,我国科教文卫事业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也曾受到左的倾向的严重伤害:遗传学、优生学和新人口论,心理学和气功研究的横遭批判即是例证。误解和偏见令我们错失了真理,在这十年浩劫中就再也明显不过了。人们正是从大批判文章的字里行间才得知,美苏两国竞相把人体潜能实验搬上宇宙飞船和大洋深处的潜艇。试想,在“克克必较”的航天计划中,竟能列入这类研究,还不发人深省吗?对于科盲和文痞的嘲骂,白发长者痛心疾首,莘莘学子更感到必须急起直追。正是这股可贵的潜流,在唐雨功能的报道之后,象火山爆发般地喷涌而出。尽管偏见的寒流再次袭来,但科学的春天毕竟降临了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春风,振奋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精神,鼓舞他们突破禁区,在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的精心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严密而卓有成效的实验研究,摆事实、讲道理地开展科学争鸣。 早在六十年代初,根据当时国外有关研究动向的点滴报道,笔者坚定地投身于生物电子学领域,并对脑际遥感的史例及可能性探索深感兴趣。经长期坚持搜集这方面的史料并初步考析后,笔者倾向于认为:各类人体潜能既非当代奇迹,也无需向国外引进,因为可以从我国浩瀚的古籍中找到大量确凿的记载。它们既历史地存在过,就必现实地存在着,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实验室研究去确认其真实性并进行古今印证。这些初步的见解除连载于《人体特异功能通讯》8~30期(1981.4~1982.12)的拙文外,还以《脑部信息遥感的考证与探索》为题于1981年5月在重庆举行的全国人体科学讨论会上报告,随后摘要发表。这一观点有幸得到钱学森同志的支持。他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更提出古实验学应是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之一,并倡导开展人体科学的研究。他的这一系列论述,使我们对古实验学研究“述往事、思来者”的深远意义有了崭新的认识,鼓舞笔者更有计划、有系统地耕耘于人体科学古实验学园地。 我国至少有七千年的文明史,公元前811年起有了世界上最早的编年史。殷墟甲骨卜辞的出土,特别是新近考定的古青铜铭文表明,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少于五千年。从数万发掘点出土的实物资料及千百万卷古籍,构成了极为丰富的文化沉积,显然个人即使究其毕生的精力,也无法尽涉其间,为了高效率地开展人体科学古实验学研究,就不能仅依靠翻书之偶得,而应从系统科学的高度,采用优化的检索策略,根据近十年探索实践,笔者愿将自己奉行的“3S、5WH”方略在此简介如下。 笔者建议将全部中国历史资料划分为三大史料系统: (1)中央(或宫廷档案)史料系统:这里记载了华夏文明史的主脉,举世闻名的中国正史(即25史)是该系统的轴心。这些历代相治的官修正史,历来为治史者所必读。加上卷帙浩繁的各朝实录,帝王起居注之类,构成巨大的中央史料库; (2)地方档案史料系统:几乎每一省、府、州、县乃至大镇、名山都有地方志。这一相沿近二千年的优秀史学传统是中国所特有的。它们载有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各阶层人物的传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平民百姓或高僧道长的,保存着不少有价值的功能者记载。各省的通志(每部达近千卷)是其主干。据估计,我国各类方志的总量约八千余种,十万余卷,这是庞大而独特的地方档案库; (3)私家著述史料系统:我国历代学者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亲历、亲闻和亲身感受,大多直书胸臆,较少矫饰或铜臭污染,其中往往有很详尽的人体异能著录。其中的精品被珍藏于我国的十大图书馆之内。近四十年来,海峡两岸各有关出版社分别选粹出版了历代笔记大观一类的大部头丛书,堪称是这一私家著述库中的杰出代表。 每一史料系统估计有几十亿汉字的信息量,很多原稿还是手抄本,它们已成为文化珍宝故极难借阅。这三大史料系统既独立又相关。业已发现,某些人体特异能事例,先被某位古代学者著录后,可被其他人的笔记所征引,也有被选入当地的方志甚至该朝的正史之中(这往往是该作者身故后很久的事)。笔者认为:以正史作经,方志作纬,可以织成雄浑的人体科学史锦缎,而笔记史料就如洒布其间的绚丽花朵。笔者业已编录有序的千例异能史料,恰好按相同的比例分别采自这三大史料系统。无论是这些史例发生时间上的连贯性,或是发生地点的广泛性,或是功能者所属民族、性别和年龄的多样性,都雄辩地证明人体异能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普遍性,这确是被传统偏见所忽视的人的潜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往日的新闻。5WH,借用自新闻的五大要素,在考析每例史实时也应对此透彻分析: (1)何人(who):这是各史例中的主角,由于古人的名号称谓十分复杂,故除校读原文外,必须查考多种文史工具书,以弄清主人公们的真实姓名、年龄、职业、生卒及其社会关系; (2)何时(when):各史例发生的确切年代也是一大要素。古代记载常用天干地支或帝王年号,要把这些简略的纪年换算成统一的公历是必须的步骤; (3)何地(where):每条史例中涉及的古地名必须正确判读并核定,更重要的是查考各该时期的历史地图集。对于脑际遥感史例而言,确认该史例所涉及两地的正确位置和其间的直线距离就在评价该史例时有重要意义; (4)何事(what):每一史例所包含的特定内容,应尽可能参校相关史传核查、弄清其龙去脉。如遥视透视的具体细节,遥感所发生的心理水平,预言某历史事件的真实性等等; (5)何故(why):各史例发生的原因、背景及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同样应尽可能予以查清和核实。 笔者在长期考析中体会到,检索并确认每一史例已属不易,而要对每一史例弄清这五个WH就更加困难。有时为了查清一则数百字记载的某一WH,往往要参阅多种相关史籍和工具书,答案可能只寥寥数语,但所费工夫是远比该史例的采集为多的。当然这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所必须的。 唐诗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却很少有人通读由二千余作者写成的近五万首《全唐诗》;但即便不是诗人、文学家,甚至初通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也能背诵几首唐诗,这恐怕归功于历代诗人选粹的《唐诗三百首》。同理,为着消除对人体科学的历史偏见或误解,恢复其历史原貌,笔者谨将从上述三大史料系统的主干中选取的,又尽可能查清其5WH的千余人体异能史例(自1985年起连载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杂志),再精选出三百例,详加注释、语译,陆续介绍给广大读者。它们已有相当的代表性。当然。若组织力量、分工合作,有计划地深入研究,还可能有更新的发现。 值得指出的是,中外人体异能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逐步形成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上商旅、僧侣和隐士们的足迹。本书选取了若干移居中国的古天竺高僧的神功绝技,他们因此而名垂青史。同样期待从他国的古文献中发现中国方士或取经者们显示异能的记载。 如上所述,国外对人体异能的研究已有百余年,但文字记载表明中国人对此的关注至少有两千年。自发特异体验遍布于各朝代、各阶层人士之中,不受民族和地域的限制,是史不绝书的客观存在。那些出于师承信仰,刻苦修炼而成的强功能者或愤世嫉俗、隐居深山、屡诏不应,或浪迹江湖、交游公卿,出入宫廷,是代不乏人的历史现象。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古代中国向世界文明贡献了近半数的发明和发现。不久前他指导写作了《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一书,确令人叹为观止。在进行一番中外比较之后,我们发现,几乎当代报道的自发特异体验及强功能者的实验,都能找到同类型的中国史例,相信其中必蕴含更多的世界第一(如名医扁鹊的透视遥诊、郑子产母子遥感、西汉名臣张良的却谷食气、东方朔的透视射覆等等)。而某些稀贵的、未见近代报道或现代实验确认的异能类型(如遥控、遥救护、脑信息相干、误遥感等),犹如当年元素周期表中的空白,将引导并期待今后重新发现和再证实。由此可见,人体科学古实验学给当代研究者提供了古今印证和以古启今的用武之地。毋容讳言,同中国近代科技落后一样,当西方从搜集特异体验报告进行实验室专项研究阶段时,腐败的满清王朝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使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特异功能者依然流寓民间,自生自灭,除了继续留下一些事实记载外,未能进步为实验探索和自觉应用的阶段。以致在当代数千种Psi著述中,鲜见中国研究者的作品。由此,我们应提高民族自信心,更应增强时代紧迫感,以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锐利武器,正确对待华夏古老文明的遗产,剥开其神秘的外壳,剖取合理的内核,为创建人体科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所述,不过粗略地勾画出正在崛起中的“古实验学”的若干侧面。在各门科学技术与历史学的交界处,迫切需要两种素质的耕耘者:懂得历史考证的科技工作者和至少通晓一门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的文史学家。 由此,自然使人联想起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他原从事生物化学和胚胎学的研究,却在风华正茂的37岁,以极大的毅力从头学中文,钻中国故纸堆。他刻苦钻研终于精通古汉语,阅读了大量史籍、地方志,作了二万多张卡片。他计划写作七大卷二十册《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出版首卷以来,至今已经近九旬,依然勤奋工作。一个外国人,竟把五十多年的宝贵光阴和心血,倾注在研究中国古老文明的科学事业上,既令人感佩又发人深思: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一历史遗产、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迎接21世纪的科学革命呢? |
| 相关文章 | |
| 中国人体科学热潮30周年座谈会 | 人体科学古试验学初探 | 超心理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 | 国外特异现象研究点滴 | 美国心理学家揭秘:人类临死时的十四种感受 | 世界超心理现象讨论 |